中澳关系陷入最低谷,澳大利亚反华抱美?澳大利亚如今勇气可嘉
最近这段时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正处于数十年来的最低谷时期。政治上的冷遇,必然会或多多少地影响经济贸易上的往来。中澳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不可或缺地与地缘政治有关。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丹•提恩正有改善两国经贸来往之意,今年四月,他要求本国企业“挺身而出”,修复对华关系,并更好地与亚洲展开接触。4月8日,他发布了一则亚洲协会澳大利亚中心和澳大利亚工商理事会的最终联合报告,其题目为《第二次机会:澳大利亚团队如何能在亚洲取胜》。

在报告中提到,“尽管发生了新冠疫情,而且围绕中国的崛起出现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但与亚洲加强经济接触的理由并没有消失。事实上,经济和地缘战略力量都在拉近澳大利亚与我们亚洲邻国的关系。因此,当务之急是学会驾驭更复杂的对华关系,确保两国展开建设性接触工作,必须成为优先要务。”为什么这份报告如此强调地缘政治?这与中澳关系又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中澳地缘政治对于双边关系格局的影响。

近几年来,中澳关系可谓是乌云密布,虽然双方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政治经济摩擦不断。澳大利亚屡屡挑衅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上,它是全球第一个禁止华为参加建设5G的国家,在新冠病毒源头调查上,它又是主动挑起“独立调查”的先锋,在南海问题上,它又甚至公开否认中国对于南海的合法权益,这些事例将澳大利亚的反华情绪明明白白的写在脸上。
在中美竞争中,澳大利亚明明可以不与任何一方形成捆绑,在具体问题上相对支持某一方的标准,维持动态平衡。但他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选边站队”,对中国的姿态一直是进攻型,这无疑是对双方信任的损耗,故意要引起摩擦。这样的失衡局面,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说到澳大利亚的平衡外交,我们就要从它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外交遗产讲起。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四面环海,独处于南半球的大洋洲,既远离亚洲大陆,也够不上美洲大陆。在经济方面,受限于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且人口有限,国内市场狭小,因此澳大利亚对于国际市场的依赖度相当的高,对外贸易占比也极大。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澳大利亚与外界贸易博弈的砝码。20世纪下半叶,东亚迅速工业化,使得亚洲区域成为澳大利亚持续繁荣的基础和主要的经济机遇。日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丰富的资源需求,这也使得澳大利亚与中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经贸联系。

而在政治方面,澳大利亚却自我认同为一个彻彻底底的西方国家,不仅坚持着西方国家的身份,还充分肯定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由于脱胎于英国的殖民地,澳大利亚承袭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法律制度等。英国和美国先后被视为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在1901年澳大利亚独立后,它是选择支持了英国。
随后,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以及二战期间英国在东南亚的羞辱退却,澳大利亚由与英国结盟转向了美国。1951年,澳大利亚与美国签订了《澳新美同盟条约》,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各项海外军事活动,步步追随美国,可谓是始终坚持与西方大国结盟。自从二战以来,它先后参与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包括两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所说,为了确保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拥有安全的环境,澳大利亚必须要寻找一个“大而强”的朋友来保证国家安全。

澳大利亚作为位于亚太的西方国家,一直努力寻求在地理和文化、亚洲与西方、经济与安全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以此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这就是平衡外交了。从专业点的角度上来看,所谓平衡外交,就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外交政策。放在澳大利亚的语境里,就是在地缘安全方面,和军事实力强大的美国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在地缘经济方面,选择和经济快速增长,且市场广阔的中国保持友好伙伴关系。在两者之间谨慎避免“选边站队”,从而达到外交平衡。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澳大利亚是如何定位身份,却在外交关系上最终走向失衡的?
作为一个年轻国家,澳大利亚的外交手段并不是很老练,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缺乏经验的。从历史上看,它的对外战略一直都是采取一边倒,要么朝向美国,要么朝向英国,直接选边站队,一旦遇到大国博弈,就很难从中找到平衡点。地处远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南太平洋,澳大利亚自然相当关切亚太地区。为了进一步维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安全,1996年,澳大利亚与美国签署了《关于21世纪澳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悉尼联合安全声明》,在2007年,澳大利亚又与日本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一边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对话,寻求寻求与日本合作的新途径。如此看来,加强与西方大国的结盟关系,站队西方的外交意图无疑显而易见。

上述是在政治方面的综合考量,而在经济方面,澳大利亚又将战略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不断发展自己的地缘经济。早在197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高夫•惠特拉姆就决定开始融入亚洲的进程。随着亚洲国家的一步步崛起,澳大利亚逐渐认识到,澳大利亚的未来取决于亚洲,而非欧洲。
中澳之间在2003年《中国工业腾飞——东亚面临挑战》中,作者就是时任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长亚历山大•唐纳,此时他就提出了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最大受益国。2009年2月,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又在2012年10月,澳大利亚又发布了《亚洲世纪的澳大利亚》白皮书,正式明确阐释了要在经济和战略层次上融入亚洲这样一个新立场。2014年11月17日,中澳两国有效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于2015年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曾多次表示:
“中美战略竞争升级并非不可避免,因而澳大利亚无需在历史和地理之间做出选择。”
然而,由于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相对实力变化以及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而日渐焦虑的情绪逐渐占为上风。从2016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逐渐开始偏离平衡的轨道。反华声音不断,对华外交逐渐走向失衡,在中美之间“选边”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态度逐渐趋于强硬。地缘政治优先于地缘经济逐步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主导因素。
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原来持超然姿态,但之后立场逐步有失偏颇。2016年二月,在澳大利亚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了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源于“对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不安”,不是将中国第一位亚太秩序的挑战者。2016年七月,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判决结果出台,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紧随美国,横加指责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放弃了以往客观的中立立场,试图制衡中国,阻碍中国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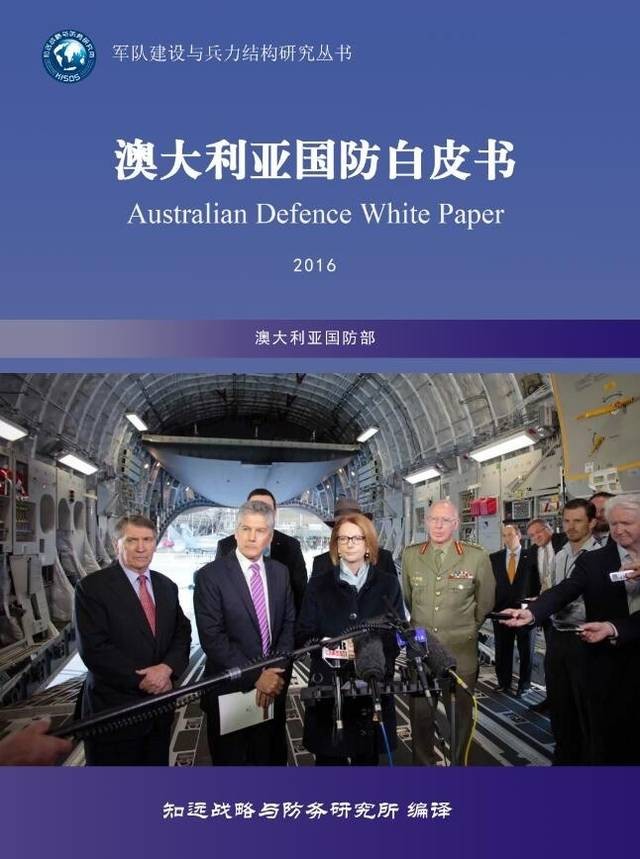
这使得中澳关系面临严重的挑战。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问题,澳大利亚原先态度是积极参与,而随后转向消极抵触情绪。2018年2月18日,据澳方媒体透露,澳总理特恩布尔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商讨构建“一带一路”提议的替代选择。两国的经贸摩擦也开始增多,尽管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中国,但它还是先后对华发起三次反倾销调查,反对中国参与其5G计划。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又试图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展开所谓的“独立国际调查”。

无端指责中国“干涉澳洲内政”,大肆渲染“中国干涉论”“中国渗透论”和“中国威胁论”,成为澳大利亚对华主基调。一边享受着与中国贸易带来的巨大商业利润,另一边又厚颜无耻地将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商业投资污名化,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这样的澳大利亚不可不谓让人心寒。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澳关系恶化,澳大利亚脱不开干系。如果澳方一意孤行,无疑将会付出巨额代价。
参考文献:《中澳关系:地缘政治抑或地缘经济?》马克•比森 李福建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徐善平
《中澳经贸关系需要新视角》刘卿
